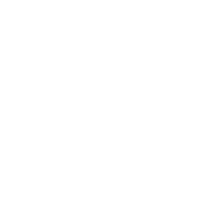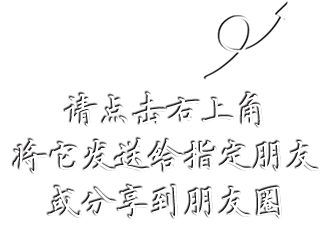散文集《遥望西域: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》(节选)
天水日报
2024年08月09日
西去的路上,除了炙热的阳光、巨大的风尘,还有隐匿于石头缝隙里的战马嘶鸣。
翻过关山,人的身体就离天空越来越近。
追求精神安慰的信徒赤脚在荆棘上走出血印;再善走的良驹也有错失前蹄的一刻,将军下马,战戟在青石板上磕出火花;商旅并不如织,驮马的铃声在干燥的空气里让人昏昏欲睡,在倾盆大雨里,人们撑起帐篷,围着篝火,会讲起一个传说中的女子:
那是后来的人们能想到的最为漫长的婚礼——从出阁到敬拜天地需要一年之久。
但在枯燥的漫漫长路上,人们热衷于谈论他们想象中的爱情。
其实并非爱情。
这是忠和义之外的另一个分叉,除了服从,主人公并无选择的余地。
第一场婚礼,发生在公元前200年。
那是汉高祖刘邦七年,那时候的皇帝还没有发明年号纪年的方法。
想起这场婚礼,人们就会想起白登山。
汉朝的帝王们对这座山十分避讳,因而,与这座山有关的很多信息均被一层一层屏蔽掉了,最后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传言。
甚至白登山在哪儿,也让后人莫衷一是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对白登山战役作了一段简要的叙述:高帝先至平城,步兵未尽到,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,七日,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。
班固在《汉书·匈奴传》中对这一节基本原文照抄。
东汉经学家服虔在阅读《汉书》的时候,对匈奴传作了批注:“登,台名,去平城七里。”其后的史学家们围绕白登山作了不厌其烦的调查研究,到近代大致出现了两个说辞,一说认为白登山是今天的采凉山,一说是今天的马铺山。
我们且不去研究这座山到底在哪儿,但我们可以看出,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,都对这座山含糊其词,服虔虽然作了标注,但只说“去平城七里”,也就是说距离今天的山西大同有七里,他仍然没有说清方位。司马迁按照惯例在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的末尾发表了太史公曰,借用孔子著《春秋》一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:“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,忌讳之辞也。”司马迁说,孔子著《春秋》,对于早期的掌故讲得很明白,但对当下的时事则很隐晦,主要是因为切近当代政治但又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东西,所以只能忌讳地一带而过。
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对决,就这样被轻描淡写了。
“今得汉地,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。”阏氏的话一语中的,点明要害。冒顿单于也明白,他还没有做好要消灭大汉的准备。两主相困,等大汉的主力援军一到,他反而会被内外夹击。于是,高明的单于将计就计,解开围困之一角,放刘邦而去。他如愿以偿地达到了震慑胁迫之效。
刘邦引兵而罢,他的豪气一点一点地塌了下去,他无奈地意识到,在他的有生之年,他再也不能奈何匈奴半分。
白登山之围后,刘邦才看清了国际形势:以羸弱积贫的汉朝与昂扬崛起的匈奴相斗,无异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愚蠢之举,而这八百却又伤不起——堂堂一国之主,出行连四匹毛色一致的马都找不到,他的将军们甚至乘着牛车上朝,这确实有损大汉威严,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
国内形势更加不妙,旧有六国的贵族后裔在秦朝末年各树一帜,形成纵横交错的军阀割据势力,大汉统一,他们虽然臣服,但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还没有及时完善建立,各异姓王心怀鬼胎,伺机而动,成为西汉政权主要的潜在威胁。白登山之围就是因为一个叫信的韩王在大同叛乱而引起的祸端。
在这种内忧外患下,只能寻求和解之法,可拿什么和解,刘邦不知道。
在白登山冻了七天七夜的刘邦,悔恨了七天七夜。大雪纷飞的夜晚,他在军帐里瑟瑟发抖,那个叫刘敬的人在他的脑袋里摇来晃去,他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大,他说:“一切都是假象。”
这确实是一场阴谋,冒顿单于也因此役而威名大震,获得了和汉室平分秋色的资本。
越是悔恨,刘邦便越是想起那个叫刘敬的人的好来。
(摘自杨逍散文《出塞的挽歌》)
自战国以来,秦人与西戎对抗,羌氐不敌而消声,大汉以后,在匈奴与大汉争霸的四百余年里,中国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几乎全被匈奴人的声音遮蔽了,这一段的历史,仿佛只有两个声音对唱,而其余的众声纵使再喧哗,也不会嘹亮,更不会清晰。
以定居农耕为主的羌氐一族,夹在两个对手的中间,与西域诸国的处境十分相似,要么投身于匈奴以求自保,要么摇摆于汉朝政府以求自全。他们在夹缝中坚毅地生存着,在刀光剑影中悄然壮大。
氐人自称为“盍稚”,“氐”是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谓。经过几百年的迁徙融合,直至魏晋以后,氐人才逐渐自称为“氐”。
西晋人孔晁写过一篇著名的《逸周书·王会篇》,详细地讲了周成王成周之会的盛况和各诸侯国的朝贡细目,提到了羌氐并对其作了注解:
周成王会见各路诸侯的时候,成王坐在坛上,面向南方,坛上挂着红帷帐,用黑色的羽毛作装饰。成王的王冠上没有垂珠,穿着八种色彩的王服,腰间插着大圭。唐叔、郇叔在他的左面,周公和太公望在他的右边,也都戴着冠冕,没有垂珠,穿着七种颜色的朝服,腰里插着笏板,他们靠近成王站在坛上。
这是一次庄严而盛大的首脑见面会,成王以八色服装区别于他人,高高在上,而他的臣子和诸侯王们则以身份的高低,分别穿着七色、五色或单色的衣服,站在下面的人都戴着冠冕且佩有垂珠。而在这次朝会中,氐族作为一个重要部落得以朝见天子。以鸾鸟上贡。
鸾鸟是古代的一种神鸟,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鸾,赤神灵之精也。”它遍身赤红,和鸡的样貌相似,能发五彩之光,鸣叫的时候能发出五个音。《淮南子·卷四地形训》中又说:“羽嘉生飞龙,飞龙生凤凰,凤凰生鸾鸟,鸾鸟生庶鸟,凡羽者生于庶鸟。”鸾鸟属于凤凰一脉,也有雌雄之分,雄的叫鸾,雌的叫和,后来把鸾鸟指代车铃。
孔晁在《逸周书·王会篇》的注解中说:“氐羌,氐地羌,羌不同,故谓之氐羌,今谓之氐矣。”氐,即是由地名而转为族名。
氐人早期生活在巴蜀和甘肃的陇西、略阳(今秦安县陇城镇及张家川县西部)一带。秦人自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而被周王封为附庸,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在陇山(今关山)以西对抗西戎。西戎是我国古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总称,其中就包括羌氐。实际上就是周王将羌氐的部分地盘分给了秦人,而彼时羌氐强大,秦人羸弱,随着秦人崛起,羌氐逐渐引退或分流。
《诗经·秦风·小戎》里说:“在其板屋,乱我心曲。”
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说:“天水、陇西,山多林木,民以板为室屋。”
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渭水》一条中,提到居住在上邽(今甘肃天水清水、张家川一带)的氐人说,他们“乡居悉以板盖屋”。因而就有了陇阺、陇坂(今关山)的地名。
氐人多居住在秦陇、巴蜀之间的峻岅相接地,因居住地分散而各自为政,所以部落众多,“有巴氐、白马氐、清水氐、略阳氐、临渭氐、沮水氐、氐、隃麋(糜)氐等。又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、白氐、蚺氐(即赤氐)等。”
中国古典文献,对于氐人的来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,一种说氐是从羌中分离出来,是羌的另一分支;一种又说他们只是地盘上的邻居,关系密切但又各自独立。但不管怎么说,他们杂居共处,因而后人便将他们以“羌氐”统称。
(摘自杨逍散文《氐人的荣光》)
杨逍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小说200余万字,多篇作品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刊转载并入选若干选本。获山东文学奖、林语堂散文奖等。出版小说集《天黑请回家》、历史文化散文集《遥望西域》等6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