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家的二月二
天水日报
2025年03月01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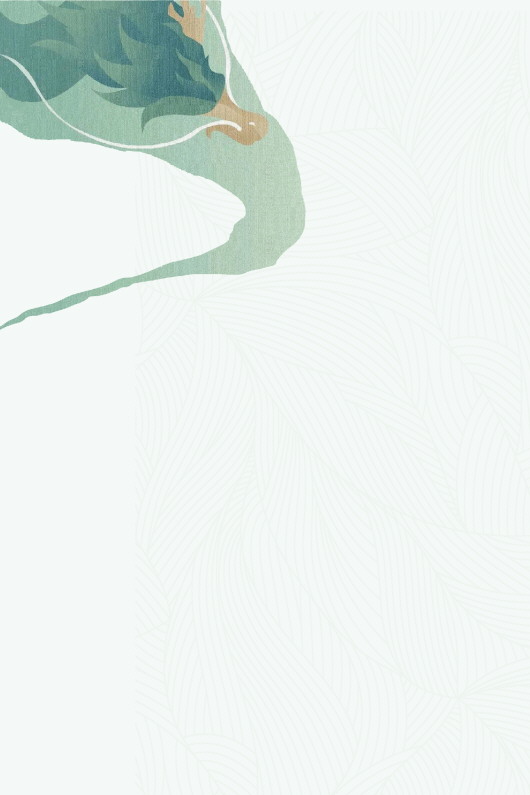
□ 王托弟
有些节日似乎只和家乡有关。比如上九,再比如二月二。
这些节日虽然不及春节、正月十五、五月五、八月十五那般盛大,但在我的心中它们依然非常隆重。每次都觉得有大事要发生,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做准备,像要迎接一个盛大的仪式。
离开家乡后,这些只和家乡有关的节日就像农历这一传统历法一样,被我遗忘在了那个西北小镇,除非有人提及或自己闲来无事翻看日历,寻常日子很少能想起它们来。
想起来又如何?
是啊,想起来也没用,还不如别想起来。
像二月二这样的日子对于离家的我,想不起来的确更好,否则,置身这孤寂的城市想起曾经的欢闹场景,除了增加一些没用的忧思外,一点好处也没有。
可是,现在的社会,要真正遗忘一件事是很难的,尤其像我这样的人,存着老家好几千人的联 系方式,翻看朋友圈的消息,不到十条就有二月二的图文。打开自己的群,“五营生活”的闫公子连常营村戏场的照片都发出来了:照片中,王湾村赫然闯入我的眼中!这个时候,再怎么假装,都知道是二月二了。
二月二,龙抬头。
在我度过的所有二月二里,二月二龙抬不抬头,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只关心这天有啥好吃的、好玩的;没有,我可要大哭一 场。不止二十多年前的我是这样的,二十年后的今天,我两岁多的侄女听她奶奶扬言“二月二不给你买豌豆了”,也像过去的我那样急得直哭。任凭时代变迁,那些还没消失的节日,在每个孩子心中都是如此的神圣!
在我老家,每逢二月二家家都要炒豆子,有些地方还有打灰簸箕的习俗,常营村还有秦腔演出;当然,大人小孩最好理一下头发。
炒豆子,据说非常具有仪式感。必须在黎明前就要炒好。待豆子炒熟了,乘麻雀儿还没飞出窝巢,用簸箕端出来,向院子的四周撒。一边撒一边念:“豆花开,豆花香,大人吃了家兴旺,娃娃吃了快成长,雀儿吃了眼无光,蛆蛆虫虫吃了全死光。”
可能是以前人们的物质生活太贫乏了,生怕有麻雀或蛆蛆虫虫从人的嘴里抢食,现在听来,这些台词简直太恶毒了——人要活,麻雀儿和蛆虫也要活嘛。所以,相对于这句,我更喜欢另一句念词:“金豆豆,银豆豆,豆豆花开又丰收。”无论如何,念词中关于人的寄寓都是温厚的,那种期盼五谷丰登、人丁兴旺的强烈愿景,赤裸裸地,甚至不加修饰地彰显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里。
循环往复,几遍念完,一粒粒豆花像金黄的碎花点缀在院子的每一块地方。大人撒豆 子的仪式一结束,就有孩子蹲下去在地上捡 豆花吃,豆渣子和黄土沾满了嘴角,依然不亦乐乎。
我妈每年都炒豆子,然而,她从来没有撒过一次豆子,真是遗憾极了。此外,我妈炒的豆子我都不怎么吃:不管是大豆还是黄豆、豌豆、玉米,我基本都嚼不动。看着他人咬得嘎嘣响,我就学别人串豆锁:用一根线将豆子串起来戴在脖子上玩。
牙齿不好的我,二月二前夕或当天,就只能眼巴巴地盼望有爆玉米花的人进村,最好是许墩村的那个赵叔叔,他爆的玉米花特别大,轻轻一咬就碎了。而那个赵叔叔,他好像也懂得我的期盼,几乎每年二月二快到时,就来我们王湾村,生意非常好,有时候三天都爆不完呢。我妈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吃爆玉米花,每次都爆七八锅,急得排在后面的人乱嚷。
据说,打灰簸箕比撒豆子还具有仪式感,可我还是没有亲眼见过。
听我爸说,跟炒豆子由家庭主妇负责不同,打灰簸箕必须由男主人进行;仍然在黎明之前,但要在撒豆子之后。这天,每家的男主人早早地就把灶膛里的草木灰勾出来,待晾冷后用簸箕盛上,端到院子里先向老天爷磕头,再开始绕院子撒一圈,一直撒到牲口棚和厕所才结束。撒灰时也有念词:“二月二,龙抬头,蛆蛆虫虫别抬头;要抬头,一簸箕打在灰里头。”一边念一边用手掌敲打簸箕沿。
和撒豆子寓意五谷丰登、人丁兴旺不同,打灰簸箕则寓意杀虫灭菌,期盼家里清洁、家人身心健康。
虽然撒豆子和打灰簸箕我没有亲眼见过,但常营村的秦腔我却看过好几次。
常营村是我们陇城镇的一个大村。村里有个堡子,叫常平堡。常平堡敬有一个因保家卫园而英勇牺牲的英雄,人们尊为“乱世爷”——每个有堡子的村子,都有一段跟乱世和英雄有关的故事。每年二月二,以常营村为中心,连同周围七八个庄头的村民在常平堡举办庙会、请剧团唱秦腔,晚上还要放自家研制的烟花。和陇城镇正月十五、三月十九、八月十五举办的庙会相比,常平堡的庙会简直太小了,但依然有很多从清水河甚至秦安县其他地方远道而来的人来朝会。
理头发,简直太日常了,日常到很难将它和某个节日联系起来。不过,在有讲究的人那里,二月二这天理个发可是大有来头的:这天理发不叫理发,而叫“剃龙头”!所以,不管有无必要都要修剪几下;尤其要给孩子理发,剪个“喜头”好成长,长大后还能出人头地呢。
我原以为不止我老家——而是整个中国,甚至全世界——二月二这天都要炒豆子、打灰簸箕、举办庙会、理头发,都有一个盛大的仪式。可是,离开家乡到北京学习生活将近十二年,竟从未过过这个节日。
这多少让我有些唏嘘,也更让我怀念曾在故乡清水河完整经历的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仪式:金黄的炒豆在铁锅里跳跃,扬灰的簸箕画出祈福的弧线,庙会的喧闹裹着春寒扑面而来……
当豆香散尽,庙会收摊,清水河畔的春节余韵便随着融冰悄然流逝。土地解冻的簌簌声中,农具与土地的对话重新响起,人们躬身耕耘的姿态,恰似二月春风里最庄重的仪式——用汗滴为时光刻下新的年轮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