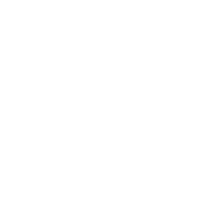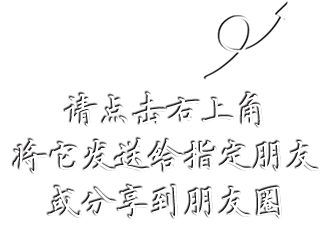丁香,童年褶皱的乡愁
天水日报
2025年05月10日
□ 白燕燕
春风掠过轩辕故里的晨昏,轻轻旋开漫山遍野的丁香盏,清水这座小城也在四月的褶皱里舒展成紫色星河。
晨曦,漫步至北山的丁香园,花枝颤动的细响,将童年的记忆拉得柔软绵长。此时,北山还笼罩在薄霜里,我已嗅到若有似无的甜——那是丁香花用嫩蕊顶开冻土的信号,是童年最稔熟的春信,是我和阿姐的丁香情结。
那时,长谷河的山坡是野花的疆场,丁香以甜香加冕为王。我们唤它“棒棒花”,指甲盖大的紫铃铛悬在翡翠枝丫间,风一吹就簌簌摇晃。六岁那年,阿姐教我辨认花苞,我们趴在苜蓿地里,鼻尖几乎触到花瓣,看阳光在花盏上流淌,听蜜蜂振翅。
自那以后,放学后的山坡上总有我们雀跃的身影——踮脚采花时衣角沾满草籽,掌心被花茎划出淡红的痕,书包里的玻璃瓶还在渴望着被“填满”,却浑然不觉已至黄昏,母亲在庄子口的喊声响彻山谷。小心翼翼捧回的玻璃瓶里不仅有花束,还有半瓶摇晃的山泉水,和少年们呼哧带喘的欢喜。当紫色花穗浸透水光,整座土屋都漫起甜醺醺的雾,连檐下的燕巢都仿佛沾了蜜,成了童年最清甜的记忆。
母亲说:“你们呀,把整个春天都灌进瓶子里了。”夜里起风,花枝敲打窗纸沙沙响,我梦见自己和阿姐变成两只小甲虫,跌进紫色的波浪里,被甜香托着漂向星群。
十五岁那年,父亲用自行车载着铺盖卷,送我去县城高中住校。后车架上的帆布包颠呀颠,掉出装满丁香花的玻璃瓶,渐行渐远消失在眼角。车过老家的长谷河后坡时,我忽然想起阿姐远嫁时说的话:“丁香花落了会结籽,我们也会‘结籽’,风一吹就飘去远方,说不定我也能落到你念书的城里。”
岁月在花影间打马而过,故乡的轮廓渐次模糊,唯有那缕甜香始终蛰伏在童年褶皱深处。大学毕业后,再回清水工作时,闻过更多的是写字楼前紫丁香的寡淡香气,却再未遇见过那种带着土腥味的甜。如今,北山的丁香园已成了时光的琥珀,各种品种在此织就成紫色穹顶,白沙镇的粉白丁香是春神轻捻的绢纱,温泉岭的野生紫丁香则如泼墨山水,土门梁的“外来物种”沿着山势洇开十里香痕。花团锦簇处,每朵花都盛着阳光的碎屑,像极了记忆里跳动的烛火。
置身北山的花海时,旧年的气息突然漫过心底。恍惚看见扎羊角辫的阿姐在山坡上奔跑,碎花裙摆沾满草汁,手中的花束抖落星点紫瓣,在身后铺成通往童年的小径。那时并肩摘花的阿姐,如今已离开土屋,唯有花香,将过往与当下酿成一杯醇厚的丁香花酒。我固执地在花海里寻找着老家后坡的“棒棒花”,想再看看那五瓣花盏上凝着的露珠,它像极了阿姐出嫁时眼角的泪。戴望舒笔下“结着愁怨的姑娘”,或许正是这花香织就的心事——它藏着时光的褶皱,却也在褶皱里藏着永不褪色的春天。
暮色漫过花枝,我终于读懂:每朵丁香都是故乡的信笺,每缕香息都是岁月的纽带,系着游子的归心。风掠过花海,而我站在浪声里,听花开的声音说:此心安处,便是故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