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见山河(代序)
天水日报
2025年05月17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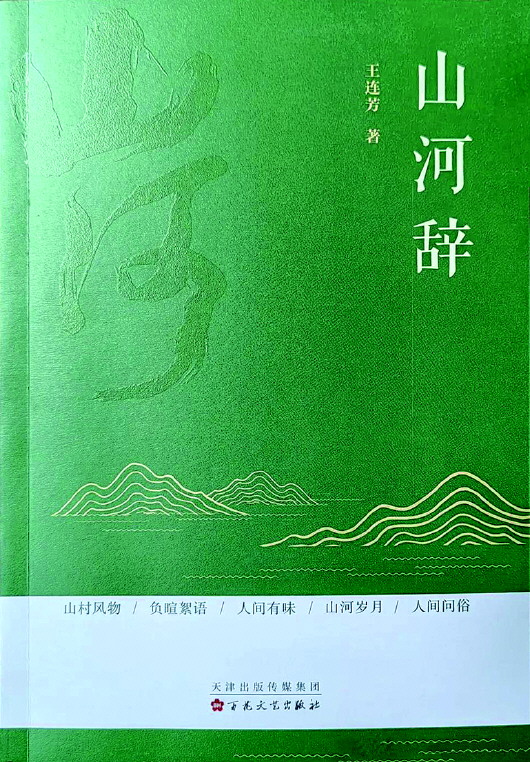
□ 王选
连芳嘱我为其新书写序。我拖拉许久,倒不是不写,写是要写,毕竟答应了。可一来琐事缠身,二来也心虚,序言这等事,似乎要大讲道理、一本正经才是,可这正是我所欠缺,三来一直不知该写点啥。可也不能因着这些缘由,而误了出书。即便如此,也拖延了月余。实在惭愧。
我在天水那会,与文友聚,有人说清水一作者文风和我颇像,我倒好奇,他们推送我数篇文章,细细一看,确有几分相似,不论所写之事物,还是用词、情绪。这位作者就是连芳。印象中,我没见过连芳,也或许见过,但一定是在应酬场中,我没有留意。当然,这都次要,见没见过,仅是表象,而读了文章,则不仅是见过,也算是相识了。
连芳是清水王河人。王河我没去过,但名字倒很亲切,一则王河也“姓王”,我亦姓王,王家人相见,分外眼热,二则我有朋友是王河人,人多才,又醇善。如此,去不去王河,倒也无关紧要,翻看连芳文稿,从她所写一景一物、一食一味、一人一事中,可觉王河和我那生养之地——麦村极为相似,或者说,就是同一地方,仅是名字不同罢了。那个地方,就是故园。
我们都是从故园出走之人,一走,便是半生,或二十年。我们借居于城市,在水泥、玻璃、钢铁、预制品、防腐剂和内卷中活着,可依然眷恋着那片土地,依然在梦里回到丛林、回到河畔、回到麦田、回到苜蓿深处、回到亲人梦中。但现实,我们却又无法回去,不能回去,不会回去。这应该是现代人所患的“通病”,我们仅是写出来而已。为什么会有此病?一言难尽,或许,唯有阅读这些文字,那长长短短的篇章,才是答案。
连芳也定是深陷回忆之人。回忆是一方旧池塘。养着过去的生老病死、喜怒离合。站立于池塘中,双脚深陷,而四顾却又茫然。回忆还是一堆五谷杂粮。养着故去的亲朋好友、乡风民俗。站立于杂粮边,内心沉沉,而长风又吹散了念想。可她同我一般,还是那么固执,要在回忆中打捞点什么,即便是徒劳,可似乎又抓住了点什么,即便纸上得来,满是故旧荒唐词句,可依然着了痕迹,刺了斑疤。
连芳关于故园旧人旧事,是会写的,也是写得好的。她写王河旧人,如常顺、三女儿、商商等,皆为我们所熟知却又漠视,她却用笔墨为他们画像、填墨、留存。其中,三女儿唱戏一段,更是词句生动、拿捏到位,人物形象,立于笔端。她还写故园饮食,我也写过,甚至为此写了一本书,故多留意了一番,我发现有些细节,连芳比我写得更为详尽,这或许跟女性对食物天然的敏感有关,也跟她的生活经验有关。我们自然有所区别,而相同之处甚多,这种相同,便是对乡味彻骨的惦念。
当然,连芳文章,文字利落,跟王河人一样,直爽;篇幅精短,倒跟清水县城一样,地方不大,可生趣处颇多;情绪饱满,这更像清水人喝酒,肝胆相照,客人要醉,我也得醉,最后,主客皆醉,相扶而出,呕天吐地,我们称此种行为乃实诚。我二十来岁当记者,去清水采访,每次都喝醉。
自然,连芳文章,也有不足之处,我想有必要点出来,就是每篇约三千字,如此体量,多少对文章有所影响,诸如叙事、写人,这种影响便导致少了细节。少了细节,文章便有铺排之嫌。文如看山不喜平。当然,这对大多写作者而言,属共性问题,在此点到,大家斟酌。
此外,写故乡之作,多如汗牛充栋,要写好,并非易事,以前农村,大都生活相似,经验相近,所以,旧事新写,写出新意,也值得我们斟酌。
看完连芳书稿,似有故地重游之感,那些人事,多已远去,甚至湮没于尘埃。时代变迁之迅速,让人目不暇接,亦万分惶恐,可人仅是时代车轮上的一粒尘土,要么随着轮子向前滚去,要么被轮子甩出时代轨道。如此想来,让人唏嘘,也让人无奈。好在还有这些文字,如港湾一般,在孤困时,在沉沦时,在喧嚣时,翻几页,读几行,且算疗伤。这或许也是文学的意义之一吧。
昨晚,兰州下了雨,想清水也是。春日迟迟,寒意仍在。抬头左望,兰山雪白,云缠山顶。想清水王河背阴处,亦有隔年积雪未化。而春雨落,王河山上亦有白雾缠住群山吧。看到景,想到人,想到文,虽有距离之隔,可方块字、人之心情、故园情怀定是相通的。相通就好,这世间,多是隔膜,而相通者,也是寥寥。
我向来不善作序,也非贤达名士,从不装模作样,也不喜粉墨登场。既已应允,便不可草率。且以此千把来字,作个序言吧。至于我如何褒贬,如何引介,文章,还需读者一篇篇读,日子,还需一天天过。于大多数人而言,写者,坦诚就好,读者,走心便足。
书名:《山河辞》
作者:王连芳 著
出版: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