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陇右到岭表(二题)
□安国强(深圳)
天水晚报
2020年11月13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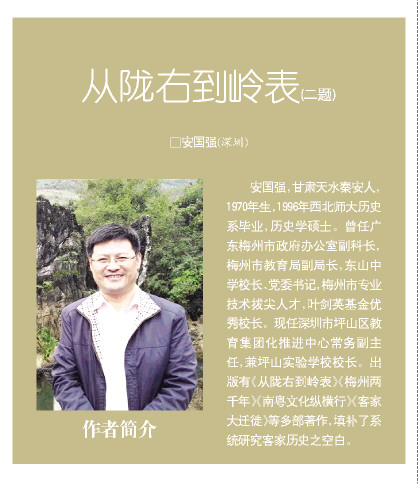

为了攀登更高的山
此生与山结缘,是一种宿命。出生在陇右黄土高坡的乱山围子里,那些馒头状的重重无名山峦,在不同季节变换着形态与衣妆,春天的烂漫山花,夏天的虫鸟争鸣,秋天的遍野金黄,冬天的银装素裹。每天睁开眼的一刹那,就放眼对面山梁上层层梯田,时时提醒自己季节的轮回与岁月的更替,遐想着山外面的美好世界,也积聚着走出大山的激情与动力。
期盼着走出大山,努力中便到了省城兰州,西部重镇,丝路明珠。但经年后才发觉,自己还是在山中穿梭。除了那数百里望不到头的秦安与省城间的重峦叠嶂,兰州,其实也是一座抬眼望见大山的城市。每每站在师大那片沙枣树林,透过沾满灰尘的树叶远眺,北山的沧桑与本真,兰山的高耸与绿意,风格迥异的美,在奔涌的黄河两岸浑然天成,与唐代诗人高适咏赞“北楼西望满晴空,积水连山胜画中”之韵味颇为神似。那山给了兰州人独特的民性禀赋,也造就一方独特的地域文化。那山给人们抵挡了凛冽西北风的吹寒,也阻挡了现代工业废气的扩散,更阻碍了人们向更大范围扩张城市的雄心壮志。
硕士毕业那年的不经意决定,使人生又一次选择了大山,来到了那千年前让北方人望而生畏的瘴疠之乡。南下广东,过惠州,到梅州,不过也很快喜欢上了那片四季常绿有花的土地。常读历史,明了唐宋以来的政治争斗,同情那些因一纸谏言或数句异见而被贬谪南荒的士大夫,他们是那么的不幸与悲凉。毕竟如苏东坡那样具有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豪气与雅量者并不多见。南宋诗人杨万里虽是出官差由西往东过岭南,“行尽天涯意未休,循州过了又梅州”,起初还能气定神闲,但到粤闽交界处,“正入万山圈子里,一山放过一山拦。”被穷山折磨得精疲力竭,几近崩溃。
千年之后的当下,世间万物沧海桑田,变幻巨大,当年的贬谪流放地已是处处人口稠密,市墟遍布,连偏远的梅州也是北人相望于途。梅州的莲花山系奇、雄、险、秀,各显其态,各美其美,迤逦千里于华南沿海,抵挡住了台风的攻势,造化成天赋的大美。乐居其中,习管理,从文教,掌学校,知乡事,访民苦,余犹未尽间,一晃便是二十余年。
有幸供职于东山中学,对东山便是一往情深。东山在小城之东,经政府多年的劈山造城,而今唯余三座小山头相连的短促一脉,居于校园之内。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东山之灵,其一在于其文化悠远绵长。数百年前王者辅创建东山书院,兴一地文风;其二在于其体态俊美毓秀。山不在大,三峰足矣,鼎立显其稳健,三可促生万物。绕行其中,使人有山重水复之妙,平缓起伏之态,远观有女性曲线之美。徜徉其上,林木茂盛处,更得饱满丰腴质感;其三在于其胸襟包容大度。体壮者信步其中,羸弱者缘坡而行,从不拒来者,其宽厚包容,非一般山之所有。
人总得向着高目标前行,如此的奋斗既充实又富有成就感。东山之巅的无数次眺望,视野的远光终于落到了西南边的深圳坪山。这座因为当年客家人的到来而变得生机勃勃,围屋遍地,如今因有蜂拥而至新客家人的到来而繁花似锦,奋进崛起。
华夏名邑,东头岭山,山环水复,桑麻翳野,近南海渔盐之便,承岭外货殖之利,闾阎相望,宜业宜居,诚天府之地。为构筑深圳东部教育高地,为建设一流全球城市,坪山发出邀请,龙聚计划开启,各地才俊,心向坪山。戊戌春日,遥接调令,乃作《浪淘沙》:千里之外坪山,东部建设正酣。碧岭西来楼无边,车如流水涌向前,风云蝶变;天下英豪开颜,共绘壮丽画卷。不拘一格佳话传,聚龙行动有新篇,美了人间。
于是在人生将近知天命之年,选择了又一座新山。
名士从来有部落,英雄时势两相需。奉命执掌坪山实验学校,此处耆硕如林,事功卓然。缺憾的是周边群楼如堵,校内低平,距马峦、聚龙等名山尚有距离。无山可依,唯借地利。胸中有丘壑,凿石堆山河。同心同德,精雕细琢,养正养志,经邦济世。夙兴夜寐,不懈奋斗于学子们灵气之培育,豪气之发轫,锐气之释放,书卷气之生成。构筑起人格之高峰,学术之高地,荣誉之高原。让实验之花开得更加妖艳,香飘四方,传扬五洲。建设坪山之实验,他年邀君再登临,渺八方,小天下。
人生就是要跨越与征服无数的山,此山不过,他山辽远。
来坪山,就是为了攀登更高的山!
做一个新客家人的本分
拙作《客家大迁徙》终于付梓面世了!回顾这二十年的创作历程,让我想起了国学大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。跟我的心路历程很是契合,故借之以承载满满的心动与行动。
曾无数次地被人问起,怎么来到梅州这大山深处,我只能说是命运机缘的安排。既然来了,便与客家结缘,这是我最大的幸运,也注定了清贫、孤独与高洁的同在。这清贫并不影响你从事事业的高尚与人格的高洁,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让人感动的人文厚重的土地上。不仅身边朋友的鼓励与支持感动着我,我在历史中也找到了学习的榜样,那就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翱。他是秦安同乡,德宗年间进士,曾任礼部郎中、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,元和四年(809)到循州当刺史。那时的循州,包括了大半个梅州,条件是极为艰苦的,时常被用来流放贬谪官员。李翱是主动来任职的,广推安居工程,教老百姓不用茅草而用陶瓦做屋,减少火灾隐患,还写了《南来录》,描述南行历程。后来大诗人李商隐也来任职。这些北方同乡身上所体现的正是盛唐文人们为国尽忠、昂扬进取的精神,时时震撼与感染着我。
选择了历史研究,注定了你是独行者。但当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了成果,或许你就成了一个引领者。我不断地在这两个身份间穿梭。不再犹豫,著书立说,藏之名山,求之不朽。终于有了多部长篇作品。当然这些成果是建立在对客家文化顶礼膜拜般的热爱之上,因为热爱,所以坚守;因为厚重,所以执着。
安顿好宁静的心灵,让浮躁去旅行。潜心去写作,既要完成数以亿字计的海量信息的收集、阅读与裁取,也要进行长幅文稿的起草、修改与润色。还要高质量完成手头繁重的政务事务,所投入的精力是十分巨大的。这清贫、孤独与高洁,便是宋代词人晏殊《蝶恋花》中所描述的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之意境。
走进历史的天空,走进客家人的世界,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知识储备、创作彷徨、生活苦闷历练过程。因有七年西北师大历史系这一老牌学科的学术修炼,对史学家勤勉治史有着嵌入式的深刻印记。时常感动于司马迁为写《史记》,以屈残之躯踏遍江淮巴蜀的坚强意志,感动于司马光为写《资治通鉴》潜心洛阳15年的执着精神。大学的恩师金宝祥、赵荧等的谆谆教诲,也激励着自己沿学术的道路前行,在专业上做最好的自己。
“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到哪里去?”法国画家保罗·高更提出的这个哲学命题确实也困扰着客家人。“客家大迁徙”课题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作畏途,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全球上亿人口的重大话题,一个牵扯数千年历史的深远记忆,一个存留万计家族谱牒中的模糊印迹。无数人反复提及,但无奈放下,皆因其太宽泛、太幽远、太庞杂。于是我下定决心,写一部《客家大迁徙》,来整体展现一次次政权力量之间的战争和平,讲述一个个家族人在旅途的悲欢离合,勾勒一幕幕民系大迁徙的壮美画卷。35章、120万字之长篇,由此新鲜出炉了。确实应了宋代词人柳永《蝶恋花》中所描述的: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瘦了绿叶,肥了红花。
宋代文豪辛弃疾在《青玉案》里有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之句,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苦苦追寻似失终得的美好意境。付出了必然会有美丽的收获。《客家大迁徙》是一部史话类作品,经历了教育部重大选题的立项和国家多部门的审读,学术意义有:一是增补了空白,冠以“客家大迁徙”之名的史话作品,乃史上第一部。二是放大了视野。三是做实了节点。使各节点的人、事、地点等要素更为有据与精准。如吴六奇作为客家成熟期的代表,他的故事在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、王士祯的《香祖笔记》等著作中都有描述,能走进全国文人的视野,他当是客家第一人。四是突出了个性。勾勒出客家人的鲜明特征:坚韧的文化传承。对自身文化传承的执着与坚守,无论走到哪里,都不忘衣冠士族的文化传统;决绝的拓殖精神。出发时背水一战,背着祖宗的遗骨上路,到达新山后是随遇而安,不断拓殖,以实力赢得空间,以文化赢得时间,天长日久,他乡成故乡;强烈的抗争意识。
《客家大迁徙》,一部奉献给全球客家人的厚礼!
作者简介
安国强,甘肃天水秦安人,1970年生,1996年西北师大历史系毕业,历史学硕士。曾任广东梅州市政府办公室副科长,梅州市教育局副局长,东山中学校长、党委书记,梅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,叶剑英基金优秀校长。现任深圳市坪山区教育集团化推进中心常务副主任,兼坪山实验学校校长。出版有《从陇右到岭表》《梅州两千年》《南粤文化纵横行》《客家大迁徙》等多部著作,填补了系统研究客家历史之空白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