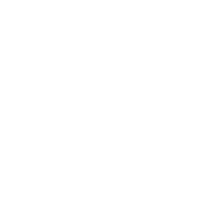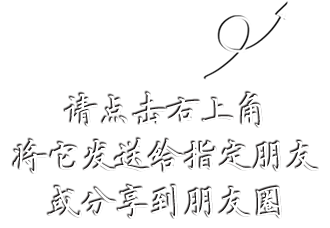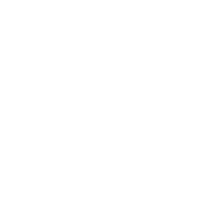遇见野兔
天水晚报
2021年05月28日


◎草间
还是三月中的某一天,早春第一波萌发的草木中,在天门山一处不起眼的角落,发现有几株疑似天仙子的青苗,它的基叶有一丝秃疮花的影子,但比秃疮花的叶子更饱满,更憨态。我一直记着,寻思在花开的时候再度寻访和确认。推算花期,正是目近,今日直奔,果然在丰硕枝叶中开出花来。
和同一区域已经花开花落的顶冰花一样,天仙子也是一株小毒草,但威力比顶冰花要高一个等级。它有着微醺醉酒般不易察觉的怪味,它的全身,根茎叶和种子都能萃取出镇痉麻痹的莨菪碱。自然界中的很多毒物,其实都是药效凌厉的苦口良药。
天仙子不远,是堇菜和顶冰花曾经的欢乐场,如今堇菜那小米粒大小的果籽在杂草中难觅影迹。但眼下收集顶冰花种子正是时候,枯干的果壳里存放着轻薄如纸的小三角形胡麻色果籽。我采折少许,发现一半已经成熟后脱落。
每次在山顶,都是浅出浅入。今天看到半山腰如星闪耀的丝叶唐松草,让我有了置身其中的冲动。一条小路边,败花的锦鸡儿灌丛下,欣喜看到一株天门冬,之前在大像山也是发现唯一一株。天门山上天门冬,算不算实至名归呢?
这个并不陡峭的山坡,明显也是被冬火焚烧过的痕迹,所有的草木都是新发的,没有枯草的混杂,让人神清气爽。目光散漫间,居然在此处发现十多株白刺花,并且恰逢热烈甚花期。它的绚烂显然是火中取栗,绝路逢生——又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例证。
满山谷弥漫着洋槐花的浓郁花香,现在也添加了一缕紫蓝白刺花的。丝叶唐松草正值青春,有梦幻的粉红蕾苞,有诗意的白色花瓣,它们睥睨着山下一个现实的世界。微风吹,是恰到好处的和煦,此刻草坡只有摇曳这个词。整个谷地的闲适和寂静,也完全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
大像山的天门冬不是孤独的,大像山的白刺花也不是孤独的……所有的生命都有呼应和期许。在这个世界,一定有一个和你心心相印、性情如一的风物。它是光,是梦,是一株互相张望而无法靠近的野草,有时也是你静坐时头顶的那片白云,有时是一声鸟鸣,它叫出了此刻你莫名突奔的喜悦。
突然,隔着一株白刺花,从树枝缝隙出现一只和我四目相对的野兔,我们彼此被对方惊摄。但我还是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,我的坐姿未变,我的呼吸如常,我连低声的咳嗽都没出一声。但我知道,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今天戴着一顶遮阳帽,可能野兔还没察觉出坐着不动的我真是个人。它依旧动作敏捷,也显然是镇定自若地从我右侧四五米距离的地方爬上山坡。让我欣喜的还是:约莫半个钟,它又沿路返回,仍然是不慌不忙的……我舍弃了打开相机的冲动,在它远离几十米之后,我仅仅拍下了它模糊的身影。
不一会儿,山谷低处的和缓山坡出现分散的好几只野兔,镜头拉近,发现他们在吃青草,刚才镜头里的一朵蓝色漏芦花头,居然被它咬断不见了。又过了一会,三只兔子同时出现在镜头中,这次我真切地看到:一只兔子将一株漏芦花头咬下来,嚼吃茎秆后把花头遗弃。这让我忽然明白有天在大像山看到的场景,满山坡有很多漏芦都是花头掉地,我一度以为是有人手贱呢。
与野兔的不期邂逅,是亲近自然的最好礼遇,是自然的最高褒奖。
我坐着的这一大段时间,耳边不时传来野鸡的鸣叫,嘎嘎两声,几分钟后又是嘎嘎两声,似乎在宣告这是属于它们的领地。我俯视这块野兔与野鸡和谐共居的浓密杂树丛,距我坐着的地方仅仅十几米,我庆幸自己的安静哑默换取了它的欢快鸣叫。
一直没有看到母野鸡的身影,公野鸡一直在这里守护,有时是一只、有时是两三只一起出没,我猜测附近应该有一处孵蛋的小窝。我没有拍到他们清晰的影像,每次反应过来,快速打开快门,它已经移位在杂草中觅食了。
接下来的时间野鸡安静很多,似乎早早归巢为安。观见四野天色微暗,就想着野鸡们应该和已经驯化的家鸡是同样习性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