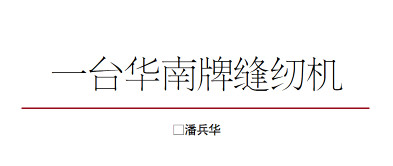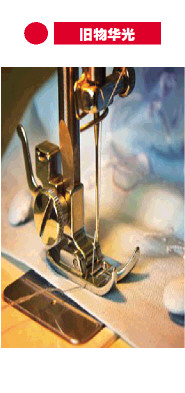一台华南牌缝纫机
天水晚报
2021年11月25日
□潘兵华
旧物华光
母亲的床头摆放着一台当桌子用的缝纫机。这台老旧的华南牌缝纫机因买不到配件,早就不能使用了。我几次要把缝纫机卖给收废品的人,母亲总是拦着说:你别管,它能占你多少地方?姊妹每次来家里,叫母亲将不能用的东西都扔掉。母亲也是一听就来火:我要是老了没有用,你们是不是把我也扔掉?
姊妹们说,母亲越老越念旧,只要她看到舒服满足就依着她。
其实,我明白母亲的心思。我们姊妹多,小的时候,要不是母亲能纺会织还自己做衣服,我们姊妹一大群,光是穿戴一项就让母亲愁死了。
以前,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。那时,母亲一年四季在生产队里劳动,抽空又纺线织布。我们姊妹的衣服几乎都是土布,而我们嫌土布粗糙难看,母亲在冬季便拿着布票去扯点机制布回来,然后给我们每人做一套的确良的褂子罩住土布棉袄。
为了让我们人人能够在过年时穿上新衣服,母亲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纺线织布和缝衣纫鞋上了。纺线车的“嗡嗡”声,织布机的“唧唧”声,纳鞋底的“唿唿”声,一年四季都在堂屋和母亲的房间响个不停。但这些重复单调的声音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如同天籁之音,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冷而又温馨的夜晚。
我家的缝纫机算是在时代浪潮中浮出的冰山一角。那时,已分田到户,农村人的干劲十足。农忙时,我们总是起五更睡半夜忙着责任田里的活路,一年两年的累积,使家里也有了余钱,我们也更爱漂亮,不愿意再穿母亲织的土布缝的衣裳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1983年的秋季,地里的作物都收进了仓,该交的公粮交了,该卖的余粮卖了,父亲和母亲便去镇上抬回了这台缝纫机。这台缝纫机花了二百多元,在当年可并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有了缝纫机,家里最高兴的要数母亲和两个姐姐了。母亲把缝纫机摆在堂屋里,又搬来大椅子,坐上去后,母亲双脚踩着踏板,前踩后压,缝纫机就哗啦啦转动起来,缝纫针像影子一样上上下下扎得飞快。母亲好不得意,对两个姐姐说,把你们要补的衣服拿来。机器缝纫的针线匀称,真比手工缝制的又快又好。
从此,母亲的空闲时间多数是在摆弄缝纫机,缝完自己的缝隔壁邻居的,补完旧的裁剪新的。母亲虽说会裁剪衣服,但做的样式并不算很好。对于开始爱美的我们,母亲只给我们裁剪裤子,上衣还是送到裁缝铺去。
两个姐姐在母亲的指点下,也会踩着缝纫机缝制衣物,遇着内衣破了,她们不劳动母亲,都自己来。母亲让二姐摆弄缝纫机的次数明显比大姐多,在母亲看来,二姐没有念过书,得寻一门手艺,学裁缝是首选。二姐长到十七、八岁,母亲就把二姐送到镇上一个熟人那里学起了裁缝。二姐拿起一根扁担,一头挑着缝纫机,一头压着石头和够吃一个月的半袋子米就走了。
可二姐在镇上只学了半年就回了家,她对母亲说,现在的人都开始买衣服穿,做衣服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,再说跟老裁缝也学不到什么新花样。二姐那时心思活泛,不甘心天天跟泥土打交道,附近村里一个和二姐同龄的女孩邀二姐去外地给做衣服的档口打工,自己带缝纫机还可以算股份。二姐挑着缝纫机去做了半年,却只挣了来回的路费,回来后她再也不提做衣服,又嚷着去镇上学理发。
时代在变,农村人也爱美了。随着科技的进步,大规模机器化生产的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,花色款式一年一个样。价廉物美的服装深受年轻人的喜爱,他们一年买几季衣服已不是稀奇事,那种“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传统早被时代的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。乡村硕果仅存的裁缝铺除了做些老年人的衣物,鲜有生意。母亲的缝纫机也渐渐成了鸡肋,只好闲置起来。
但这台华南牌缝纫机是自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后,我家置办的第一个最贵的家当,它铭刻了我们姊妹随着时代一起成长的印记。那些过去的时光,在母亲踩着缝纫机踏板,细心地缝制儿女衣衫的幸福日子里慢慢流逝;在二姐挑着它南来北往时,二姐玫瑰般的梦想之花在追赶日新月异的时代中悄然盛开。这台老缝纫机是岁月的留存,记录着新时代里,一个普通人家对幸福生活的不断追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