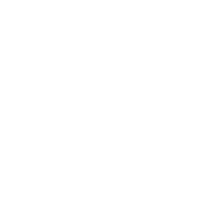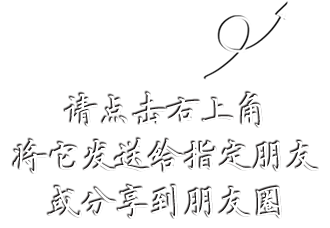灰灰菜
天水晚报
2022年10月28日

它的家族
草木,不管大小,都是自然的奇迹。自然的奇迹,不仅由参天大树召唤,它也在不起眼的小草上吟唱。了解一个事物,不仅要懂得向上看,看高贵、勇气、尊严和智慧的光辉,更要知道向下看,看到叹息、呻吟、抽泣和无奈中存在的真相。
——帕乌斯托耶夫斯基《金蔷薇》
和
□一石
春天,绿色烂漫于山野。清晨,雾气把露珠挂在草茎和花朵的眼睑上。在北方的寒气中,灰灰菜的叶面上盛着露珠,微风吹翻叶子,露出叶子背面一层晶莹的灰粉。粉背含绿,灰灰菜就是由此得名的。
一种植物的俗名能被口舌相传,这个名字一定简洁顺口,既综合了一个物种的特征和内涵,又会在这个名字里,把这个物种秉性中携带的特色摄入人心。
爷爷在世时,大姑姑每到深秋,总会给家里送来自己夏天晒制的灰灰菜。大姑姑知道爷爷喜欢吃这种野菜,那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。西北的寒冬,缺少新鲜蔬菜,她总会专门为爷爷储备一些。
多年后,城市生活将我的人生改换成另外的面目。在我住所的对面,有一家西北菜馆,菜单上看到凉拌灰灰菜,点了来吃,口味和小时候的几乎毫无二致,真是意外惊喜。品尝着灰灰菜的清爽,曾在舌尖上留下的苦涩,一下子变成了野趣。
记得大姑姑将晒干的灰灰菜浸入冷水里,这叫泡醒,再用开水泡软,捏干水渍,切成寸段,调上麻油、香油、蒜蓉、盐,拌上辣椒丝,就可以入盘。有时她会问一下爷爷:“爸爸,要放辣椒油吗?”那是要给爷爷换一换口味。放上辣椒油之后我倒喜欢吃了,灰灰菜的味道变得回味无穷。在唇齿之间,灰灰菜汁液里的苦涩滋味弥漫出来,涩味后面,又会渗出别样的甘美。
这种味觉的音乐,很难用简单、质朴、耿直的旋律,没有喧哗,也没有醉人的刺激。灰灰菜的滋味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日子,也就仅是一种野菜而已。
“拔草去喽!”记得小时候放学后,小伙伴拉长声音在家门口喊我。拔草,就是去打猪草。打猪草的时候,摘得最多的,是灰灰菜,还有反枝苋。这些野草把根扎进黄土沙地、沟渠坡洼,不惧干枯,借一点雨势就会疯长。我们在野地里边打闹边比赛拔草,在土崖中间跳跃、攀爬,释放少年的野性,和野生长的草木一起,摔打夯实生命的韧性。
我挎着竹篮,走上山间,灰灰菜在野草丛生的路旁,窥探骄阳洒遍世界,我纵身越过一堆堆土埂,跑向路径迷离的山地高处。那个时候,我并未听到灰灰菜里忧患千古的歌调,也并未意识到灰灰菜对日常生活的意义。我气喘吁吁跑过童年,跑过少年。关于灰灰菜的碎碎念遗失在路上,就像有金币遗失到时光的草丛里,将来有一天,当我去把这些大地的财富一枚一枚捡拾起来的时候,陪伴过童年的灰灰菜,是一种我生命里的植物,又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了。
灰灰菜的大家族属于藜科,藜科植物除了少部分是木本(像戈壁和盐碱草甸地带的梭梭柴)外,其余都是草本。藜科植物喜光、耐旱,它们在茂密繁盛的森林生长,但大部分都选择生长在荒凉干燥的旷野,风沙肆虐的戈壁,以及盐碱侵蚀的不毛之地,把根深深扎下去,展叶,开花,结果。
黄土高原上,藜科植物种类繁多,这里几乎聚集了中国200多种藜族植物的大部分品种。由藜科植物的分布,也可以看出西北土地的特征:干燥、荒漠化和土地盐碱化。藜科植物生长的区域,正是人与环境激烈对抗的地方。
我就是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长大的,我知道这些植物怎样和自然进行交融和呼吸,一颗童心在藜科植物的细茎中飞翔过。日后,因为机缘和爱好,以博物视角和人文美感的心去体会种种植物的存在,走入一个个国家森林公园,审视人和自然、人和环境的相互依存。
包围在自己周围乱纷纷的藜科植物,比如菊叶香藜、灰绿藜、水灰藜、猪毛菜、梭梭柴、扫帚菜(地肤)、菠菜、盐爪爪……都像是构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世界的多样性极为奇怪,不同物种的存在,就像一把打开扇子的不同褶皱,褶皱与褶皱之间可能永远都无法相见,但大家在一起组成了黎科植物的整体,这个整体会共同阻挡风沙,阻挡盐碱地的侵蚀,让生命的连续和丰盛保留下来。
借着傍晚的余晖,穿过旷野,眼前星星点点泛着金光的落日让人心潮起伏,朋友突然说:“你看,眼前一片‘野地磷火笑’。”什么是狂野深处的磷火?什么是寂静世界里的笑声?内心的琴弦突然变得尖锐起来。荒草中泛着紫红的藜,高过人的头顶。我们一直在野地里走着,荒野因眼前藜科植物的繁盛更显荒芜。旷野的荒凉穿过了黄昏的沉寂。我回味着“野地磷火笑”的鬼魅,心里涌出想要把什么东西点燃的冲动。
藜,西北方言叫灰条。遇上叫藜的人,我会认出他来自哪里,我会在他的身上感觉到和我身体里相似的勤勉和固执。
生在乡村曾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自卑,从容与多样性在我身体里曾经是枯竭的。羞涩与贫乏增加了我的封闭。为了打破困厄的囚笼,我一直在进发,没有一刻歇脚。从乡村进入城市,又从一座城市迁徙到另一座城市,又在城市里,重新接近山川与河流。不管生命之思,还是博物之识,我要求自己不断走入纵深。自己的人生就像从世界的多个平流层中间穿过。
在写作中,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从一个荒野的背景里诞生,这个背景给了我从泥土的根上开始的机会。这个起点足够低,所以让我有幸将生命的区间占得大一点。正是在逼近钢筋水泥森林的过程中,和这种森林结合又分离,完成了我人格外在与内在的打磨和塑造。朴实厚重的土地和钢筋水泥的森林横亘在内心的藩篱逐渐被打散。这个艰难的过程让我吃尽了苦头,但也正是这样的苦头,给了我从未有过的穿越感。在我的内心,乡村与城市的边界消失了。在乡村和城市的天平上,两边的砝码一直在变,我一点一点努力让外部世界在视野里扩展,让内心世界的期望不断聚集凝练到至为简单。我这样做,而且觉得唯有这样去努力,生命才值得一过。虽然令人失望的时候也不少。自己的这个秉性是不是和灰灰菜类似?把根与边界看得那么重,不在乎任何艰险。我的荒野,因我祈祷而呈现给我一股野性,在自己的骨子里沉默,同时也在大自然深处歌唱。
说起藜,说到灰灰菜这个名字,南方的朋友说:“这不是灰灰菜吗?很常见啊。”太普通,平时谁会注意,好像会开小小的紫花。朋友对灰灰菜模糊的认识同时被南方万紫千红的花海干扰了。藜科植物本就是广布荒野的草本。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里把灰灰菜身上的灰色称作“珠灰”,这名字像她的人一样冷艳。藜并不开紫花,所谓开紫色的小花只是视线里的错觉,藜幼苗的顶芽,刚刚展开时呈玫瑰的色泽,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,藜也叫胭脂菜,红心灰,就是这个原因。
菊叶香藜,在藜科植物里算是香草。菊叶香藜的叶子很漂亮,是那种长戟的式样,叶子呈肉质,一片片像模子铸造出来。叶子背面的黄色腺体能散发浓烈的香气,再配上它鹅黄的衣装,有点酒馆歌女的味道。小时候,揪一把菊叶香藜的叶子,在手上揉碎,手掌张开,手上的香味会让人始料不及。
菠菜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藜科植物,饱饮一团叶绿素会给人带来舒心的快感。
像梭梭柴、盐爪爪、猪毛菜、刺沙蓬……这些戈壁滩和盐碱地的宠儿,它们让整个藜科植物变得充满斗志。在风沙干燥的世界里,这些植物的叶子退化成肉质,来保存身体水分的蒸发,面对狂风和烈阳,叶与茎肉质、革质的进化变成了它们身穿的铠甲。它们体内的高含盐量,使得这些植物能够像高压水泵一样吸收周围环境里稀少的水分,它们体内的泌盐腺体,使它们和高盐高碱的环境建立了共生的平衡。他们懂得在恶劣环境里的生存之道,在大自然逼仄的空间里,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