酸菜的滋味
天水晚报
作者:邓书俊
新闻 时间:2021年11月23日 来源:天水晚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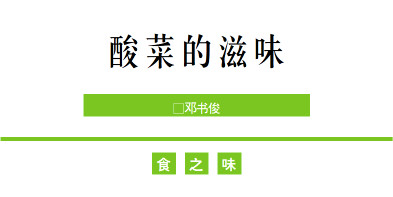
□邓书俊
身在异地,吃遍了南北饭菜,但最能够打动味蕾的,却依然是武山老家的酸菜。
酸菜,俗称浆水,是武山人人都爱的特色,现已被纳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要说起浆水的历史,那也是源远流长,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:“文王嗜菖蒲菹,孔子闻而服之。“菹”在这里的意思就是酸菜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有浆水的专门记载,说浆水“调中益气,宣和强力、止咳消食,利小便”……
武山地处西秦岭北坡,从来干旱少雨,“三年一小旱,十年一大旱”,是这里的真实写照。我们的祖辈为了填充饥饿的肚子,绞尽心思把各种野菜挖来洗净切碎,储藏在陶瓷缸里,发酵成酸菜,以度饥荒。因其味道酸香可口而深受人们的喜爱,并一代又一代流传了下来。
酸菜做法很简单。每到春天柳絮飘飞的时节,我便跟着村里的大孩子去挖苦苣、蒲公英、荠菜、苜蓿等野菜。野菜挖回来后,母亲先把野菜洗净,放入沸水里略滚,再在水中加少量面粉,连同浆水引子倒进酸菜缸里,经过三五天发酵,一缸酸香可口的酸菜就做成了。酸菜缸最好用陶缸,在我的记忆中,家家户户都有几个或大或小的陶缸,我家也不例外。那时候家里穷,因父亲有箍缸的手艺,就把碎裂的陶缸低价买来,再用细竹篾把它圈几圈箍起来,破损的缸就可以继续使用了。
在生活困难的年代,农村人一天两顿饭,几乎顿顿不离酸菜。酸菜撒饭、酸菜拌汤、酸菜搅团、酸菜馍馍。母亲做的荞面疙瘩儿很好吃,尤其是母亲用老菜烙的酸菜馍馍,现在想起来都让人馋涎欲滴。“疙瘩儿”是老家的土话,就像喊着孩子的乳名,格外亲切。荞面疙瘩儿擀起来容易,母亲常常是水烧开后才开始和面、擀面。因荞面没韧性易断,所以只能切成筷子粗细的根根,然后下到沸水锅里,打几个滚后,再从缸里舀两碗酸菜,直接倒进锅里,一锅香喷喷的荞面疙瘩儿就做好了。至于用野葱花炝浆水、吃浆水面,那是包产到户的事了。
提起老菜的酸菜馍馍,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压酸菜的情景。老家属于高寒地带,蔬菜稀缺。每年开春时节,母亲总要买点苞菜苗栽到自留地里,然后浇水施肥,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着,到秋庄稼收割上场后,母亲就开始收割压酸菜。压酸菜是越冬最重要的事,因为酸菜一直要吃到野菜长出来的时候。苞菜运回家后,全家人一起动手,择去黄叶,切成细丝,再背到山泉边清洗干净,倒入开水锅里一烫,然后用爪篱捞到陶缸里,用青石头压实,就可以保存半年不坏。母亲投酸菜时,常顺便留些老菜,用来烙酸菜馍馍。小时候的我经常帮母亲烧火,母亲先把面和好,再把老菜放进凉水里一泡,然后捞出捏干水份,放入盐油辣椒面,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馍馍有一种独特的香味,让人百吃不厌。
“武山人走到哪里,酸菜缸背到哪里。”这话虽然有些夸张,但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几年前,我因病动过一次手术,术后感冒发烧,浑身像着了火一样,丈夫给我端来省城最有名的排骨面,可我一口也吃不下去,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老家的浆水面。丈夫见我嚷嚷着要吃浆水面,便打电话给居住在省城的老乡,一个多小时后,老乡端来了一碗浆水面,吃完那碗浆水面,我顿感浑身舒服多了。
“少小之餐未易忘,每思家馔几回肠。千秋早有酸蒲苴,万户今留苣菜香。痛饮田头消暑气,深藏橱下度年荒。农家茅舍酬亲友,浆水面条最味长。”这首诗是陇上一位诗人所写,他写出了故乡游子共同的心声,又为今天的美好生活增添了一种回味。
别看浆水只是一种普通的家常味道,但它承载着游子对亲人的思念,对家乡的眷恋。无论走到哪里,这种永不泯灭的味觉记忆,都将伴我随时光慢慢老去……
食
之
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