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吃炒面的日子
天水晚报
作者:牛永明
新闻 时间:2021年12月21日 来源:天水晚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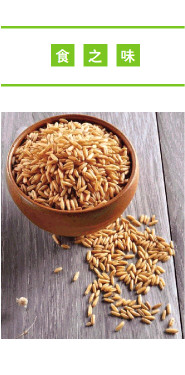

□牛永明
炒面起源于何时何地,最先由谁炒制,已不可考,但它对我们甘肃人来说是功不可没的。炒面在我的家乡武山龙川河畔叫熟面,在缺粮少食的年代,熟面就是我们的馒头和饼子,它陪伴着父老乡亲度过了艰苦的年月,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过去,家乡制作炒面的主要粮食是谷和糜,也有用燕麦的,南部山区则用青稞和大燕麦制作炒面。其中,燕麦和大燕麦熟面为上品,青稞熟面次之、谷和糜熟面为最次。制作熟面并不复杂,一般是把粮食去除杂质晒干,再用大铁锅炒熟晾凉,然后拿到磨房磨成粉即可。
与馒头和饼子相比,熟面保质期长,携带方便,是困难时期人们外出和居家的主要食物之一。在我记忆中,吃炒面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的。当时因为生活所迫,我家搬迁至漳县草地河公社三眼泉村,借居在大队部旁边的一座大房子里。
我家吃的是青稞熟面,挖小半碗,倒上开水,用筷子搅成糊状就能吃。漳县的水硬,冬天,天还没亮人就饿了,母亲便起来拌一大碗熟面,给我们兄弟四人每人捏一个“熟面狗娃”,两三轮下来,一碗熟面就吃个精光。吃饱了,再睡一觉,天才大亮。
没有吃过燕麦熟面时,我不知它的味道。当第一次吃燕麦熟面时,我才知道,世间竟还有如此美味的东西!为此,我偷偷吃过两三次大队干部寄存在我家的半袋燕麦熟面,母亲发现后告诫我别再偷吃,否则不好向人家交代。后来,母亲把我偷吃熟面的事告诉了主人。当时我很难为情,没想到那位大叔笑着说:不就一点熟面吗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我知道,其实母亲比我更难为情。
1979年腊月,我家从三眼泉搬回老家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我们的生活逐步改善,能吃上白面了。但由于家里吃饭的人多,干活的人少,每年下来,总缺一两个月的粮食。父母亲常为这事头疼,父亲面浅,通常是母亲出面,向亲戚朋友借粮食。这其间,大哥结婚,离婚,又结婚,让本不宽裕的日子愈加捉襟见肘。有一年,全家七口人靠喝清汤寡水的大燕麦粥、吃熟面过了四十多天,才熬到小麦收割。那还是上好的燕麦熟面,也吃得我直反酸水。
1986年,我考上了师范。同学们都是从农村来的,在家里敞开肚子吃惯了,一下转入定时定量的生活,短期内都难以适应。星期天更不好过,因为灶上没有早餐,只有午饭和晚饭,饭菜质量也不如平常好。附近没有饭馆,有钱也没处使,更何况同学们没有钱。第一学期中考后,父亲扛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提包来看我,里面装了一袋燕麦熟面。这袋熟面我星期天吃,晚自习下了吃,同宿舍的人吃,老乡们吃,帮我们慢慢适应了定时定量的学校生活。
去年我在一篇小说上看到,陕西老乡把甘肃人叫“炒面客”。当时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诉说的酸楚,如果有白面馒头,谁愿意去吃炒面呢!但再一想,那时用炒面客称呼甘肃人,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而且,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甘肃人乘着绿皮火车从陕西背回了多少粮食和面啊!这份兄弟情谊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于心。
今年春节期间看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,我更感受到了炒面的伟大,是炒面支撑着志愿军战士,把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赶回三八线以南,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。就一种食物的功劳而言,在新中国的历史上,真没有哪一种食物能与炒面相比。
近年来,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吃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。人们不再追求吃饱,而是探究怎样才能吃得营养、吃得健康。这不,人们又开始吃炒面了。不过,现在大家吃的都是燕麦熟面和小麦熟面,有的用白糖拌了吃,有的用蜂蜜拌着吃。看着电视,喝着罐罐茶,吃着蜂蜜拌的燕麦熟面,别提多惬意了!
食
之
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