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走出喇叭花迷宫的路径
天水晚报
作者:
新闻 时间:2022年09月02日 来源:天水晚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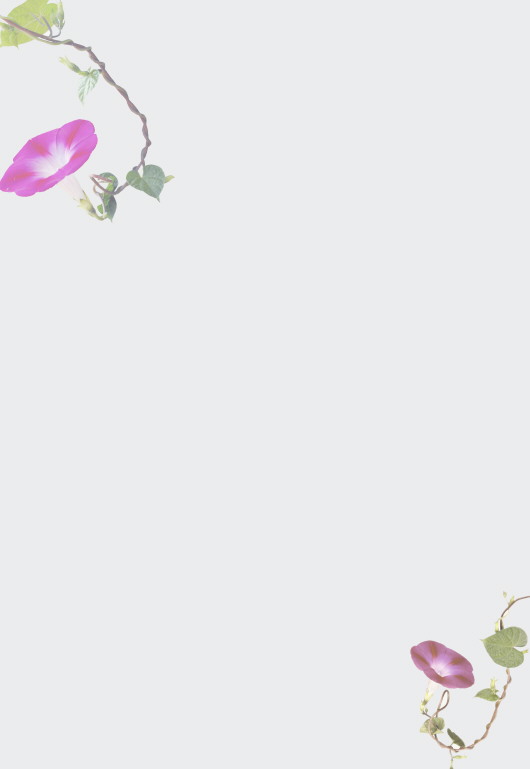
□一石
“为什么当人内心芜杂神情憔悴时,会走向郊野,把双脚踏到泥土当中?”朋友问我。
“被欲望挤压,心生厌倦,自然那双清凉的手会召唤人,为疲惫的人心恢复动力,这是人的本能吧。”朋友静静地听着我说。
——《自然日记》
“喇叭花里有迷宫吗?”
喇叭花是如此普通,应该没有人以它为载体来质问自身存在的迷结吧!
如果把喇叭花里最为常见的牵牛花、田旋花和打碗花的花朵摘了摆在一起,不是对旋花科植物细加推敲过,对植物分类完全陌生的人,在这样盛开的花朵里,要分辨出喇叭花们之间的差异,花朵相似的外形,几乎就像进入一座喇叭花的迷宫里。
走在绿绒碎花萦绕的大地上,喇叭花冷不丁跳到视野里来……旋花科的植物都可以被称为喇叭花,我曾被喇叭花的多种面目迷惑过。这些面目,有时候是银灰旋花,有时候是田旋花,有时候是打碗花(又叫小旋花),有时候是裂叶牵牛,有时候是圆叶牵牛,有时候又会是肾叶打碗花……我没有去摘这样的花儿,我只是站在盛开了喇叭花的原野当中,朝着天地相接的地平线看。这些花儿的姿态,由坚硬变得柔和,触摸着我的脚印,并和我的脚步结伴同行。经过这样的原野,就像踏在意识缥缈的云上。
和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往野外荒芜的地方走,看到野地里粉色碎白的田旋花、刺旋花和打碗花的花儿交织在一起,朋友小孩子一般的心性被惊得飞起。
“这是什么花?”在四周黄土沙砾的铺盖当中,这样的声音像是小浪花,这些小浪花里包藏的喜欢,除了抒发一点积了多日的郁闷,其实并不想要什么具体的答案。
“好像是牵牛花!”
“哪里是牵牛花,明明是打碗花。”
“知道了还问!”
“不知道尽瞎说,嘻嘻。”好像心情好了起来。
对牵牛花别样的感情,是因为“所有的喇叭花都是牵牛花”,这是从小根深蒂固的认知。围绕长在院子里的牵牛花,其中藏着一幅外婆的素描。住在时光深处的外婆,她脸庞的线条,头发的灰度,衣服惯有的漆黑深蓝,这些都像在渐变,密布在我的脑海里。
时间的深土里,牵牛花张开它扩音器一般的喇叭,我倾听草木与人同在的回音,历史,连同旧日记忆,将我的朦胧童年推入与爱相连的时光溪流里:
初春种下的几粒种子,埋到拇指深的黑土里,是陪着妈妈在早晨太阳刚刚冒着花的时候种的。春末到来,太阳晒得人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,牵牛花已经盘在上房门前搭起的竹竿上,像一个绿色的卫士。牵牛花的细茎扭得像个麻花,螺纹一样。南房门口,随人影出出进进的节奏,牵牛花鼓着劲,顺着竹竿直往屋檐顶上爬,绿茸茸的芽尖,今天探头在左边的叶子下,明天已经探头在右边嫩茎的缝隙里。
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和小狗虎子捉迷藏。
妈妈说:“今年的肥喂得及时,会开好多好多牵牛花!”
下午的落日里,外婆和穗红妈坐在屋檐下聊家常,昏沉阳光的散碎光线透过花茎叶从头顶散落,我抱着小虎,靠着外婆,打着盹,迷迷糊糊中,数着牵牛花的新芽、花苞。
第二天,发现牵牛花的绿芽已经超出昨日标记老远,惊喜中对外婆嚷起来:“婆,这个头都长到这里了,你看。”外婆停下她手里的针线活,看着我:“你快快长,牵牛花长得都比你快。”我不服气了,踮着脚尖,和牵牛比一比高低:“婆,它还没我高。”
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,我的童年是在外婆身边度过的,外婆的生活,自证着我童年的空寂与虚无,又使澎湃和丰盛充盈着我的心。偶尔,当我闭上眼睛,外婆的微笑会在幽深当中浮起来。很奇怪,我从未意识到外婆由苍老显出的枯萎。我一直认为,她从未有过一丝杂念地爱过我,自然而然,我也用相同的方式爱着她。
牵牛花上,好像附着了这样的声音,附着了外婆的语调:“你快点长,牵牛花长得都比你快。”听着这声音,我冥顽的天性里的铃铛摇动起来。
属于牵牛花的季节,它的疯长会占满院子的一角。过不了几天,风吹进房门,太阳洒在绿叶上,几天没见的绿茎,已经攀到手都够不着的地方。外婆和我逗趣:“你看,它长得比你高了吧!”我从房子里搬出大椅子,爬到椅子上,站起来,然后大声叫厨房里正被馒头的蒸汽笼在白雾中的外婆:“婆,婆,你来看,快来看!”牵牛花没我高啦,哈哈哈。我站在椅子上傻笑,我不能确定自己的屁股上是否因此留下过她的手印。
风从西北方向晃晃悠悠吹过来,我的身边,紫色的、粉红的、洁白的牵牛花,像天上星星一样围绕着,外婆一把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,脸上带着气,胸口起伏着。
和牵牛花茂盛的生命力一样,外婆抱着我的双手那么有力,那些被苦难磨砺的皱纹编织在她眼睛的周围,掩藏不住的忧郁在这些皱纹中弥漫。她生气地看着我,我胆怯地看着她。我的童年带着狡黠和难以驯服的野性,被她轻盈的目光罩着。在我心中,是外婆的怀抱,消散了我内心最初的混沌,在她的怀里,我的敏捷与洞察第一次伴随天性的直觉苏醒。
夏末,牵牛花的叶子开始凋谢,枯萎藤架结出鼓鼓的种子。靠近屋檐,遮阴的地方,还有牵牛花一朵接着一朵在开。清晨,亮晶晶的露珠迎着阳光在花瓣上打开。
我问母亲:“妈,牵牛花怎么这么能开?”
“牵牛花像你婆一样,勤快。”母亲说。
关于牵牛花深潜的记忆把我对喇叭花的认识弄迷糊了。只有在讲述旋花科植物的书籍里一种一种认过去,才发现,喇叭花的样子形成了喇叭花迷宫的入口,旋花科植物迷宫出口的路径,却要到围拢着喇叭花的叶子上才能找到。
野地里的打碗花,又叫小旋花或者兔耳草,其实叶子未必有兔子耳朵那么大,叶形狭长细小,仿佛觉得那不像是叶子了。
在福建泉州的大海边工作,曾见过肾叶打碗花,叶子很有韵致地半握成一个拳头,这种沿海地带的植物和我心里的牵牛花、田旋花对应,抚慰过我的乡愁。
田旋花,有另外一个我喜欢的名字:中国旋花。起这样的名字大概和最早在中国发现它有关。它的叶子呈狭长三角形,看上去像古代兵器谱上的戟,虽然只是缩小版的戟。
刺旋花,西北民间叫鹰爪柴。在酷烈干燥的气候当中,刺旋花的叶子退化成针形,为了避免羊和骆驼的肆意啃食,在茎上进化出了像鹰爪一样的尖刺。朋友给我发来她到贺兰山上拍摄的刺旋花的花海,成片的刺旋花交响乐一样被阳光的金手弹奏,喧腾,又静默。
我在戈壁滩上还见过一种银灰旋花,叶子也像针,只是这微微舒展开的针被银灰色的丝状绒毛包裹着。陡峭的风势在西北土地上肆掠,开满银灰旋花的土地就像披了一件银狐的袍子。
“一种造物总有一种造物生在世上的妩媚。”古话给浅浅生命的河流注入活力。
牵牛花最容易和其他旋花区别开来的,是它手掌般大大的叶子。牵牛有两种,一种是裂叶牵牛,一种是圆叶牵牛。
裂叶牵牛手掌一样的叶子,浅浅散裂,经历过心伤后的坚强,让它变得雅致、独立,有了一种从容的美。
圆叶牵牛,叶子顾名,是完整的心形。在旋花科里,它像是幸福花。大凡幸福之物,总带有柔媚的娇嫩和安然的祥和,仿佛这也是幸福的天性。
我在植物园里还见到过旋花科植物里的巨人——月光花,它像是旋花科植物里的月光女神,穿着飘逸流彩的绿叠裙,盛开的喇叭花上分泌出来粉珠一般的水滴,光影划过细密的水滴,折射的光线带起朦胧的光晕,形成一片十五当空的皎洁月色,透过这样的月色,想象和真实之影在时间的河流里交叠,人心投影在视觉中冉冉而动的幻象会悄然浮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