爬地松
天水晚报
作者:
新闻 时间:2024年07月05日 来源:天水晚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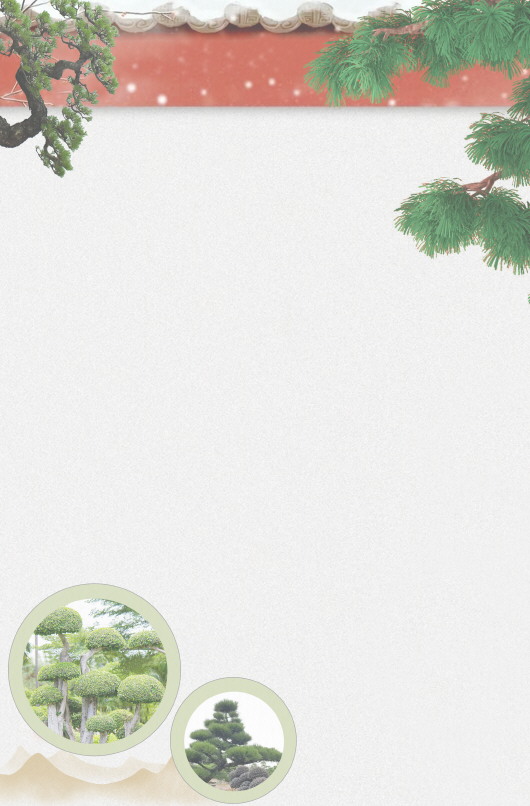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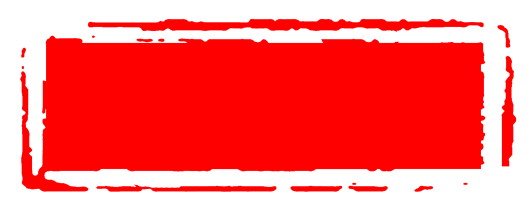
自然书
□第广龙
如果我在30岁和爬地松相遇,对这样的生存方式,我不一定赞同,但会表示理解。我已经经历了一段颠簸的人生,有得意也有失意,有不甘也有向往,严酷的生活和命运,让我懂得了适应,也不断振作精神,谋求新的机会。
◇◇◇
在我的印象里,松树无不高大挺拔,伟岸孤傲。哪里有松树扎根,即使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,也会充盈雄性的气概。我见过马尾松、白皮松、华山松,都非常笔直,是绝不弯腰的,就连主干上的枝条,也纵横着纹理,生铁一般向一个方向伸展。最让我震撼的是前年的伊春之行,我走进了红松林,如同走进了仪仗队,每一株红松,都有标尺一样的身材,都在天地间站岗似的,直入云霄,没有一丝的倾斜。暴风雨袭来,有的红松倒下了,身子依然是端直的,死去的红松,也不会示弱,更不会委屈了哪怕一寸肉身。
可是,当我在阿尔山的石塘林一带看到爬地松的那一瞬,我就在疑惑,这也叫松树吗?这和我常见的松树,有血脉上的关系吗?的确,我是极不情愿把这样的植物,和我心目中定了型的松树叠加在一起的。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啊,全部匍匐着身子,几乎没有主干,只是一根一根枝条,也就手指粗细,鞭子似的耷拉着,一朵一朵针叶依附在上头,勉强把绿的意韵展现出来,表明生命的活动没有停止。根部的颜色,是炭火烧败之后的黑,间或还凝结着团团白斑,也是大病未愈的症候。我仔细寻找,竟然没有发现一株哪怕车辕粗的,也没有选择到一棵直立于地面上的。
我真的有些失望,既然是松树家族一员,就不应该以这样的面貌出现。它体现的是凛然的硬气,这是天生的,这是从骨头上就开始硬的,在任何地域都不可改变的。从一粒种子起,从一株幼芽起,就决定了松树永远的品质。松树的一生,都高昂着头颅,哪怕泰山压顶,也是宁折不弯。只有这样,才没有辜负松树这个名称。依照以前获得的一点知识,我这样认定着松树的形象。
那么,爬地松该如何生长呢?看着四下的环境,我一时给不出一个答案。我看到的是亿万年前火山爆发后遗留的现场,一块块不规则的石头,肿瘤一般堆积在地上。石头的表面,残存着一个个漩涡状的孔洞。这是地下喷涌出来的岩浆,冷却以后凝固成的火山岩。只需简单地推断,就可以得出结论,那一场地火的席卷,即使再顽强的生命,也会在顷刻间化为灰烬。剧变之后,泥土几乎消失了,水分无法驻留了,这里还具备萌生一星绿色的条件吗?可是,爬地松如同一个异类,不知在何时,竟然来到了这里。或者说,竟然选择了这里,要进行生长的尝试。
就像我看到的这样,爬地松成功了。生命的不可能在这里转换成了可能,这的确是一个奇迹。而为此付出的代价,便是颠覆了松树一贯的形象,只能伏低身子,弱小能量,在火山石的困境,在灰尘和雨水制造的单薄的立足点,抽出一根根枝条,抓住空气中的一丝潮湿,艰难地存活下去。任何惯常的生长,在这里都会失败,都会被排除。生长不易,持续生命更难,爬地松却在这一片死寂的岩石上,一代一代传承着,与其说征服了火山岩,还不如说这是征服了自身。
假如我在20来岁看到爬地松,年轻气盛,敢于尝试和挑战,我有一个想法,会觉得爬地松活得窝囊,要生长,就高大生长,做不到也要抗争,失败了也不后悔。而且,我还会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人辩论,会觉得真理就在我这一边。如果我在30岁和爬地松相遇,对这样的生存方式,我不一定赞同,但会表示理解。我已经经历了一段颠簸的人生,有得意也有失
意,有不甘也有向往,严酷的生活和命运,让我懂得了适应,也不断振作精神,图谋新的机会。我在这个年纪看爬地松,会感到这也是一种活法,没有必要强求爬地松改变自己,也不认为把腰身挺直就是强者。可是,我看到爬地松时,已经过了不惑之年,接近50岁了,快到了知天命的人生阶段了。我有什么理由指责爬地松呢?当第一印象刻进我的脑海,有了一点最初的想法后,我陷入了沉思。爬地松能在如此境地生长,并一直延续着年轮,本身就是生命的胜利。爬地松爬在地上,并没有丢失什么,也没有因此而变得低下。而且,爬地松体现出来的,正是最可贵的品质,那就是不认输、不放弃,在石头上扎根,用生长来证明不论遭遇到多大的艰难,只要抱定要活着、要活下去的信念,照样可以抽枝展叶,开花结果。我由衷地敬佩爬地松,似乎找到了人生的一个榜样。
爬地松又名偃松、矮松、千叠松,多生长于生态脆弱,土壤贫瘠,风力强劲的高海拔环境,高3-6米,是四季常绿植物。这是我了解到的一点介绍。我走在火山岩形成的地貌上,身边的爬地松,以它自己的习性,感应着天冷天热,展示出一丛丛绿色的枝条。生命本身的美好,同样属于它。
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可笑,所有的评价和看法,都是人附加给爬地松的,爬地松只是按照自己的基因密码生活着,繁衍着,爬地松只是它自己。对于种种褒贬,爬地松不知道,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因为,这些冲突的说法,所谓的意义,对于爬地松都是无效的,与爬地松也是完全不相关的。对于爬地松来说,存在就是一切,它只服从自然的法则。